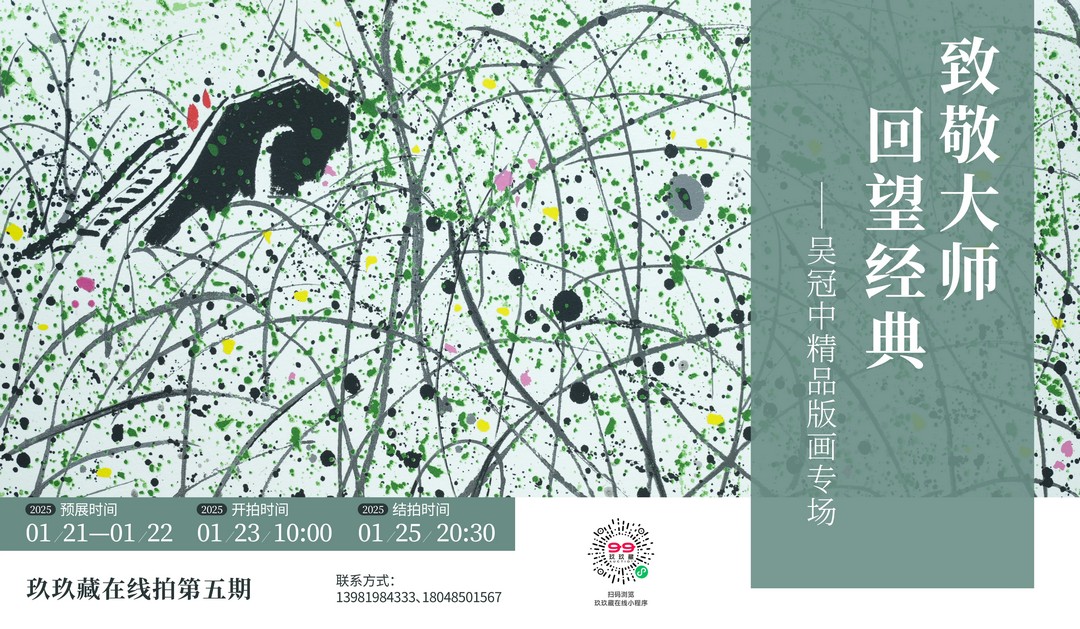當(dāng)我們面對一幅抽象畫,看到的是什么?色彩、線條還是帶有節(jié)奏感的音符?抽象畫拓荒者康定斯基的答案是:“有一種藝術(shù),不再是重現(xiàn)物質(zhì)世界,而是通過抽象幾何形狀的和諧與不和諧,以及色彩的力量,與觀眾進行一場視覺上的精神共鳴?!?
看完上海西岸美術(shù)館和法國蓬皮杜中心推出的“抽象藝術(shù)先驅(qū):康定斯基”展覽,的確讓人找到了一些共振,那些不明意義的繪畫符號,伴著創(chuàng)作者崎嶇的人生,似乎讓人看到了一些藏在畫布背后的東西:那是康定斯基渴望展現(xiàn)內(nèi)心,卻又不甘束縛的表達,也是理性思考的大腦與熱愛藝術(shù)的心靈的碰撞,他創(chuàng)造的“抽象繪畫”概念推動了20世紀(jì)及21世紀(jì)的藝術(shù)發(fā)展,被寫進了歷史。
半路從藝
1866年,瓦西里·康定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個富裕的家庭,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對繪畫和音樂的興趣深深植入內(nèi)心。但在30歲之前,他從未接受過專業(yè)的藝術(shù)教育,也從沒想過會成為一名藝術(shù)家。這時,學(xué)習(xí)法律和經(jīng)濟出身的康定斯基在大學(xué)教書,還經(jīng)營過一家印刷公司,生活平靜而富足。
他第一次感受到藝術(shù)震撼來自于去觀看法國印象派展覽,那次在莫斯科舉辦的展覽中,康定斯基看到莫奈的《干草堆》,他沒有立刻認出這幅畫的主題,這使他感到非常迷惑和驚奇。另一次,他在莫斯科皇家劇院觀看了瓦格納的《羅恩格林》,全新的編曲深深地震撼了他,讓他第一次有了“聽到畫面”的感覺,日后康定斯基打通音樂與繪畫的界限,正是這場音樂會帶來的啟蒙。
1896年,康定斯基30歲的時候,他決定放棄教職,成為一名畫家。他職業(yè)生涯的轉(zhuǎn)變改變的不僅是自己的人生,還有整個藝術(shù)史的進程。
康定斯基的畫家生涯始于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慕尼黑,進入美術(shù)學(xué)院學(xué)習(xí)。在慕尼黑,他感受到了繪畫的生機,這里誕生的“青年風(fēng)格”與反學(xué)院派的法國“新藝術(shù)”運動遙相呼應(yīng),年輕人憎惡虛偽,熱衷于美好的畫面。
在這個時期,康定斯基接受油畫、雕刻訓(xùn)練,嘗試各種藝術(shù)形式,就像一個孩子充分體會著色彩帶來的愉悅。他喜歡描繪戶外的景色,忠于光影帶給眼睛直觀的感受,畫面中干燥的黃土路面和云朵投下的影子,明顯帶有印象派的氣息。除了畫風(fēng)景,騎士和俄羅斯民間傳說也出現(xiàn)在康定斯基的畫中。受到浮世繪風(fēng)靡歐洲的影響,康定斯基研習(xí)了版畫技術(shù),尤其是木版畫的創(chuàng)作。他也繪制蛋彩畫,在深色背景上平涂大量彩色區(qū)域。無論是木版畫還是蛋彩畫,看似毫不相關(guān)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其實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將圖案平面化、分離色彩區(qū)域,這些都為康定斯基日后的抽象畫創(chuàng)作做了鋪墊。
在展覽的第二部分“初始:技藝研習(xí)”板塊,我們能看到康定斯基這一時期的作品。1904年,康定斯基與第一任伴侶布里埃爾·蒙特開啟了穿越歐洲、遠抵突尼斯之旅,展覽中這幅《突尼斯街景》便是旅途中的創(chuàng)作。他充滿活力的筆觸和明亮的色彩讓人聯(lián)想到后印象派的風(fēng)格,他認為比起物體的形態(tài)本身,我們的記憶記錄的更多是物件的顏色。
1906年創(chuàng)作的紙板蛋彩畫《歌》也是這一時期令人矚目的作品。畫面中繪有色彩鮮艷、有著裝飾圖案的長船,船夫身著俄羅斯傳統(tǒng)服飾,水面和倒影用點塊狀的色彩表現(xiàn),顯示了康定斯基對民間藝術(shù)的興趣。

《歌》 1906年 光面紙板蛋彩 
《即興Ⅲ》 1909年 
《灰色之中》 1919年 布面油畫 
《作曲Ⅸ》 1923年 布面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