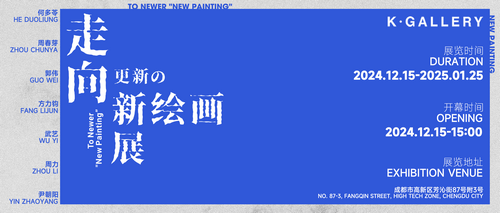在吳作人的藝術(shù)經(jīng)歷中,一共有過三次“晚畫會”。
一曰“曾家?guī)r晚畫會”,1940年于吳作人在抗戰(zhàn)陪都重慶之住所舉行,基本上是幾位青年美術(shù)家專為吳作人安排的一項(xiàng)“康復(fù)療養(yǎng)活動”,其時,吳作人在戰(zhàn)火中新逢喪妻(李娜)失子之人倫慘變,又因過度悲傷罹患眼疾。曾家?guī)r晚畫會使吳作人很快振作起來,原本有可能開“戰(zhàn)時文藝之新風(fēng)氣”,無奈,晚畫會因戰(zhàn)火毀家而起,又因戰(zhàn)火毀家而終。國運(yùn)如此,夫復(fù)何言。
二曰“洋溢胡同晚畫會”,1946至1947年于北平宋步云寓所舉行,冠以“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畫室”之名。時值山河光復(fù),“全局之勝,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藝專復(fù)員開學(xué),安置不少教員在洋溢胡同居住,晚畫會在同仁切磋技藝之余也自然成為諸位芳鄰的閑時小聚,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無奈,好景不長,因吳作人與執(zhí)政當(dāng)局失和,遠(yuǎn)避英倫,晚畫會頓失砥柱,草草收場。
三曰“水磨胡同晚畫會”(“十張紙齋”),1953至1957年于北京水磨胡同49號吳作人與蕭淑芳的住所舉行。新朝氣象,國祚日隆,天下太平。一時間,水磨胡同人文薈萃,晚畫會集素描、油畫、水彩、水墨各專業(yè)之海內(nèi)高手,更有文化藝術(shù)界各路名流趨之若鶩,“文藝復(fù)興”,于斯為盛。水磨胡同晚畫會所被賦予之意義,也早已超越美術(shù)和文藝本身,成為“政通人和”的典范。無奈,盛極而衰,與“蘇式美術(shù)”一統(tǒng)江湖正相反,“十張紙齋”門外車馬漸稀,敗象漸露,至“反右”風(fēng)暴驟起,遂告壽終正寢,迄今五十年矣。
縱觀三次晚畫會,與純系“無組織,無紀(jì)律”的曾家?guī)r不同,自洋溢胡同起,因發(fā)軔于國立藝專體系之內(nèi),始得到徐悲鴻的重視,贊許,乃至支持,為實(shí)踐徐氏“提倡寫實(shí),學(xué)好素描,打好基礎(chǔ)”的理想園地,吳作人不見容于舊政權(quán)而出洋韜晦,亦為徐氏刻意保全之功?!笆畯埣堼S”則占盡天時、地利、人和,豎起了“實(shí)踐悲鴻主張”的大旗。
然而,有史以來,恐怕素描引起的爭論從未如此復(fù)雜和尖銳——它原是基本功,但被“形而上”之后,就成了不學(xué)它便根本不配學(xué)藝術(shù);可是學(xué)好了素描,表現(xiàn)人還是表現(xiàn)自然又成了問題;待至“蘇式素描”泰山壓頂之時,“全因素”和“提煉取舍”的觀念又將“素描論者”割裂為不同的陣營;還有,千萬不能忘記,管它哪種素描,和中國畫之間的“別扭”,從頭到尾,貫穿始終……
三次晚畫會,三次無奈。
吳先生,我們的“十張紙齋主人”,及其“‘和而不同’的同志”,關(guān)于“民族化的油畫”和“推陳出新的國畫”,做到了一代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也付出了一代人所能付出的一切;他們不能抗拒三千年以來的黨同伐異之風(fēng),也解脫不了“秋風(fēng)中第一片落葉”的宿命,所謂“家國共命運(yùn)”之說,可以解嘲。
“十張紙齋”作為“一首余音繞梁的小夜曲”,曾經(jīng)并且仍然以“和而不同”撥動著人們的心弦,激發(fā)起人們心中最深沉的回響。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
《十張紙齋(1953—1957)——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個案》總撰稿人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