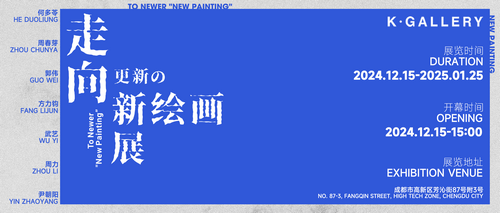川美油畫77級的同學(xué)曾經(jīng)有二十位,干嘛用“曾經(jīng)”二字?因為在1979年,其中有兩位分別考上了本院的油畫、國畫研究生,而使得本班慘遭減員至十八位,此二位就是:何多苓與黃同江。
說到黃同江,索性先聊他,以表對同江兄的悼念——他是第一個永遠(yuǎn)離開了我們的老同學(xué),英年早逝,不勝悲痛挽惜!黃兄是本班年長者之一,來自川北地區(qū),平時低調(diào)謙和不善言談。79年他努力跨進(jìn)研究生的行列,是先油畫后國畫,然后是超越專業(yè)、跨行成功的典范。畢業(yè)后他少與同學(xué)們往來,在四川教育學(xué)院任職,潛心研習(xí)各種繪畫,正準(zhǔn)備再攀藝術(shù)高峰時,不幸患病于前些年去逝,可惜、可惜!
何多苓——在所有的油畫班同學(xué)當(dāng)中是“最像”藝術(shù)家的,他具有以前許多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俄國文學(xué))當(dāng)中所描述的全部“藝術(shù)家”之特質(zhì):長長卷卷的頭發(fā),瘦條的身材再配上一雙細(xì)細(xì)的手指,略顯倦怠的臉上閃爍著憂郁而多情的眼神……由于他“歐化”的外表及有些古怪、靦腆且散慢而又隨和的性情,因此格外的討人喜歡,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們的追捧!當(dāng)然,那只是外表,而實質(zhì)上他也是被公認(rèn)的“才子型”的藝術(shù)家。在班里他是最具有“小資”情調(diào)者之一,他天生一付不錯的嗓音,又彈得一手好吉他。記得某個仲夏之夜忽聽到他與幾個小兄弟在寢室里用吉他彈奏著一首俄羅斯小曲,再配上低吟、同步的男聲四重唱,哇!那美妙無比的歌聲、琴聲頓時飄出窗外,蕩漾在美院的夜空之中……還記得當(dāng)年他教會了班里所有人唱蘇聯(lián)的“騎兵進(jìn)行曲”,乃至一發(fā)不可收拾地唱成了77級油畫的“班歌”!的確,他相當(dāng)?shù)母挥性娨馇艺{(diào)侃,從他嘴里創(chuàng)造出了許多后來流行于世的精典語言,最著名的是:“粉子”。在繪畫方面的才能與做為就不用我去提了,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史里都少不了他。
羅中立——這個名字隨著他創(chuàng)作的《父親》一道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在二十多年反反復(fù)復(fù)的頌揚之中,《父親》與其作者“羅中立同志”相提并論、緊并而不可分割,且已經(jīng)牢牢地成為了一塊響當(dāng)當(dāng)?shù)慕鹱终信疲£P(guān)于羅中立、羅兒兄、羅院長的故事相當(dāng)多,各種版本都有,寫得夠細(xì)夠深入的當(dāng)屬川美王林先生的那本《當(dāng)代中國的美術(shù)狀態(tài)》一書,其中這樣描述到:“同學(xué)的成功深深刺激了羅中立,他入校以來,潛心于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成績一般,素描平平,教油畫的老師對他頗感失望,從連環(huán)畫轉(zhuǎn)向油畫,最初只是因為同學(xué)的油畫得了獎,就像小時候兄弟得了父親的贊譽,羅中立妒嫉得很,求勝心切,他決心好好畫一張來證實自已的油畫能力……”。羅中立真是很不簡單!一個著名的畫家,做院長,管著那么多事情:抓創(chuàng)作、抓教學(xué)、抓房子……一抓就是快十年,如果沒有“兩下子”能行嗎?
程叢林——他的故事一開始就被陳丹青講過了,另外本人亦在《回憶·自省與批評》文稿當(dāng)中專題寫到過他,此處就不再贅述,而將其“版面”讓給別的同學(xué)。
張曉剛——在校期間沒有任何跡像表明他是會在日后成大氣候的人物。在整個四年當(dāng)中,他表現(xiàn)一般:習(xí)作平平,創(chuàng)作平平。雖然在川派“第三次浪潮”中忽見他的《藏女》身上出現(xiàn)了“凡高”的氣質(zhì),但很快就消失并轉(zhuǎn)型了。那是重啟國門,改革開放的初期,許多的新玩藝兒一下子涌了進(jìn)來,擋都擋不住。在藝術(shù)上更是五花八門—整個西方美術(shù)史都忽然的降臨下來,砸在中國藝術(shù)青年們的頭上,著實的令人有些二暈二暈的。曉剛的性格偏陰柔,為人相當(dāng)?shù)钠胶停f話時總是慢慢、柔柔、笑咪咪的。沒有任何“進(jìn)攻性”;僅管他的才華從不寫在臉上,但心里絕對是很有數(shù)的。記得有一日他一板一眼地說到在云南下鄉(xiāng)遭遇到“鬼”的故事時,一臉的陰沉,嚴(yán)肅得像似真的有鬼魂附體,令人毛骨悚然!嚇得在場的女生禁不住尖叫起來……的確,在他后來創(chuàng)作的《血緣·家庭》系列當(dāng)中,那幽靈般的形象,實在令我吃驚不?。禾瘛⑻窳?!——旁人肯定不知道我的意思,不知道那段“鬼魂靈”的故事。我心里暗暗佩服:好一個鬼才!
莫也——一個相當(dāng)“老坎”且文言文氣十足的名字,配在了這位川北宜賓“小花”妹妹的身上(都說莫也酷似年青時的陳沖,就是八十年代《小花》里的女主角)。她和川美78級油畫的劉虹同學(xué)均被中國美術(shù)界稱其為本院美女級的“才女”,尤其是畢業(yè)后莫也曾去到過北方:先后在中央美院和天津美院都待過,這可了得?北方漢子們哪里領(lǐng)教過這等聰慧伶俐的西南女子的風(fēng)彩?以至于我十多年后返回國內(nèi),遇見諸位美院老先生時還在念念不忘:“真沒想到在你們班里還藏有這樣的一個才女!”的確,由于之前本班的幾位“重量級”老哥的名氣太大、人氣太旺,總也擋著“小花”,所以才造成了姍姍來遲來的被發(fā)現(xiàn)。然而,莫也就是莫也,她終歸會以她自已渾身的靈氣與才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飛得更高走得更遠(yuǎn)!
楊謙——“謙兒”號稱77級油畫班的“小神童”,入校時僅只十八歲、論年齡他排在本班倒數(shù)第x位,但各科成績卻絕對是名列前茅。想當(dāng)年高考成績一確定,消息就不禁傳出:“哎呀!不得了,考分最高的是個十幾歲的成都崽兒,考成了雙甲!”(注:當(dāng)時川美考題兩門:素描和創(chuàng)作,平均分?jǐn)?shù)以甲、乙、丙、丁劃出級別)這消息相當(dāng)?shù)亓钗页泽@,因為之前本人雖不看好自已臨時抱佛腳的那套偽“科班”石膏素描成績,但對“創(chuàng)作”,心中還是自信“無敵”的??韶M料半路殺出個“雙甲”小子!所以,我一直好奇很想見識這位“神童”。神童就是神童,果真與眾不同:中等身材,著深色呢制大衣,挺拔合體(那年頭國人的服裝普遍不合身):微卷的中長發(fā)下生得一張白凈文氣的臉,在他“學(xué)者型”的眼鏡片下透著自信、理智與冷漠的神情:還有那小而豐滿的嘴唇,時不時地會吹奏出貝多芬、莫扎特等大師名曲、交響曲。是的,他“小資”味兒十足,酷愛音樂,拉得一手好琴(小提琴),常常獨自陶醉在他的音樂當(dāng)中……的確,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進(jìn)入到他的世界里。他性格內(nèi)向獨往獨來(據(jù)說“天才”一般都這樣),后來才發(fā)現(xiàn)他躲避眾人是在背英文單詞,那會兒他已經(jīng)啃完了《大學(xué)基礎(chǔ)英語》第x冊,而我們才剛剛開始ABC!確實,那種精神,那等水平,至今無人可及,無人可攀——那年月的人,大都憨傻愚木,尤其是像他那個年齡段的人,更是活在云里霧里,而“神童”則不然,他與超常人的冷靜面對周遭無序吵雜的一切,摒棄干擾,一步一步地去計劃著、努力著,去實現(xiàn)自已的夢想—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葉,“謙兒”遠(yuǎn)渡重洋到達(dá)彼岸與他失散很久的奶奶及先于他之行而移居美國的父母和家人團(tuán)聚。川美像他這樣具有“學(xué)究”氣質(zhì)的畫畫人不多,他亦是目前于77級油畫班當(dāng)中,唯一真正的、硬碰硬的,獲取到美利堅合眾國藝術(shù)碩士學(xué)位的同學(xué)。
周春芽——不在77級油畫班的“花名冊”上,他是77級繪畫系版畫專業(yè)的學(xué)生。這些“細(xì)節(jié)”外面很少有人完全清楚,然而這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春芽以及其他年級、其他專業(yè)的王亥、王川等同學(xué),都成為了“川派”乃至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的領(lǐng)軍人物。春芽是最具“形像魅力”的四川畫家,他天生一副好儀表、好身材、好性格,使他幸運地免去了那些由于基因里缺少點兒什么的人,所有的煩惱和郁悶,因此而顯得格外地身心健康。第一次見到春芽就羨慕得很:一米八高的個兒,白里透紅的皮膚,溫文而雅的性格,哇!好一個東方的美男子!他讓我立馬想到《南征北戰(zhàn)》中的“高營長”——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中國電影的大明星馮杰,儒雅高貴而樸實。如果換用今日的偶像做比喻,他應(yīng)該屬于金城武那一類的大帥哥型。其實,春芽真正的魅力還是在他的藝術(shù)上、色彩上。陳丹青就多次在不同的場合稱贊過春芽的《藏族新一代》和《剪羊毛》,他說:沒想到“藏族人還能這么畫”,“畫出那么多的色彩和筆觸來”。我的色彩開竅很晚,因此特別佩服天生色感好的人。1979年我剛完成《為什么》之后仍意猶未盡,很想再畫些“文革”題材,于是,就拉著春芽畫起了連環(huán)畫《血染的早晨》。那是個“文革”中兄弟相互搞“武斗”的悲劇故事,來源于“川大”民辦的《綿江》雜志,可惜不久“傷痕”時代結(jié)束,那雜志也被迫??覀兊摹斑B環(huán)畫”亦不了了之了。如今,每每想起與春芽的那次“未遂”的合作,同時又會想起那個傷心而黑暗的一幕:1987年,當(dāng)我出國后第一次返回川美母校時,偶然在一樓道角落里堆放垃圾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趕火車》與《剪羊毛》!它們已經(jīng)“傷痕”累累,遍體是污、色彩脫落,幾乎面全非……那是一個藝術(shù)品“無價”的年代,畫者只管興趣著、畫著自已的畫,全然顧不得“產(chǎn)品”的“出路”與處境。悲哀,悲哀!
陳安鍵——是班里的“小兄弟”,與當(dāng)年77級油畫班上的幾個“大腕兒”相比,哪方面都?。耗挲g小、個頭小、膽子小、名份就更小了,有人調(diào)侃:他能考進(jìn)這個“名星班”,簡直就是個“奇跡”。安鍵樸實無華與世無爭,見人三分笑,相當(dāng)?shù)乜蓯?如有他佩服的大兄弟需要幫忙,他會心甘情愿地跑前跑后,毫無怨言。安鍵的臉長得很有特點,有些“美國大兵”感,我一入校就發(fā)現(xiàn)了,于是就將他畫進(jìn)了《為什么》。后來程叢林也“迷”上了這張臉,分別畫在了好幾幅作品里,似乎百畫不大厭。早年的安鍵由于各種因素起步較晚,“三次浪潮”都沒趕上亦失去了不少的機會。僅管他心里也想追、想趕,可必竟是速度太快,相差太遠(yuǎn)!所以,總體的狀況還是:想畫點什么就畫點什么,能畫出點什么就畫出點什么;就像趕火車誤了點,反正趕不上,索性也就不急了,慢慢來吧。二十年后,忽然一日看到安鍵的《茶館》系列,頓時讓老同學(xué)們個個刮目相看!雖然,這“奇跡”姍姍來遲,但它必竟是安鍵在藝術(shù)上的飛躍,是可喜可賀的!從此,安鍵的世界五彩繽紛了:教學(xué)、畫展、賣畫……讓他名利雙收,人也自信起來。不過,老同學(xué)們的手也沒閑著、腳步也沒停下來。我的《趕火車》拍賣創(chuàng)紀(jì)錄之后,安鍵在電話中說:“真想不到高兄會梅開二度!”接著繼續(xù)感嘆:“以前我們追你們像是去追星星月亮,眼看著就要追上,一下子你們又跑到了火星,看來這輩子是沒得希望再追上了……?!?
班里的同學(xué)還很多,這才談了二分之一都不到,就是已經(jīng)談到的這幾位亦顯得不夠:不夠深、不夠準(zhǔn),總之是不夠“豐滿”。希望:如果一不留神讀到自已“故事”的老同學(xué),多多見諒!我當(dāng)然還會繼續(xù)接著談同學(xué)往事的。